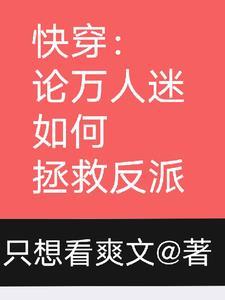笔趣乐>穿成败家女?我拒绝摆烂带飞全家 > 第28章 练武(第1页)
第28章 练武(第1页)
暮春细雨沾湿檐角铜铃时,沈嘉岁将大戏楼图纸铺在花梨木案上。工匠老刘眯着眼凑近油灯,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羊皮纸上摩挲:“小姐这图样倒是新鲜,只这戏台子尺寸…”
他比划着丈量手势,“怕是要用上等红松木才撑得住。”
沈嘉岁以手支颐,护甲在图纸上划出浅浅痕迹:“明日便动工罢。”
忽又想起什么,转头吩咐紫莺:“传话下去,府里会识字算账的皆可来试掌柜账房。”
消息像火星子溅进油锅,半日便烧遍侯府各个角落。
次日天未大亮,沈嘉岁的青玉院已挤满人。
穿绸缎的管事与粗布短打的家丁摩肩接踵,连马厩喂草的老丁都搓着手站在角落。
“倒是我小瞧了。”沈嘉岁倚着缠枝莲纹凭几轻笑。
她原以为侯府这些家生子早被富贵泡软了骨头,谁料乌泱泱竟站了二十三人。有总角小儿踮脚张望,也有鬓角斑白的老仆攥着衣角。
紫莺捧着香炉过来添香:“小姐不知,自打您提拔了茶楼那位小子,府里多少双眼睛盯着呢。”
沉香屑落在青砖上,惊得前排小厮缩了缩脖子。
沈嘉岁执起青玉狼毫:“头一桩考写字。”她目光扫过人群,“不拘写什么,能见人便好。”
墨香在宣纸上晕开时,老丁佝偻的背忽然挺直。
他舔了舔开裂的指尖,工工整整写下“丁守业”三字。最后一捺尚未收笔,身后便传来嗤笑:“老丁头这字比鸡爪子划拉的还丑!”
沈嘉岁拾起那张墨迹未干的纸。字虽歪扭,却一笔一画透着郑重。
反观那嘲笑人的年轻管事,纸上“周福”二字糊成一团墨疙瘩。
“周管事请回罢。”她将纸轻飘飘一掷,“鸡爪子尚知轻重,您这手…”未尽之言化作轻笑,臊得那管事涨红脸夺门而出。
日头爬上檐角时,院中只剩八人。
紫莺捧着算筹过来:“第二桩考算数。”她展开题纸念道:“今有绢每匹价三贯,买五匹赠一匹…”
老丁蹲在青石板上划拉,粗粝指腹磨出血痕。一炷香将尽时,他颤巍巍递上答纸:“共需十二贯五百文。”
沈嘉岁扫过其余七张错漏百出的纸,忽觉额角直跳。原以为能挑出三五个得力人手,谁料尽是些酒囊饭袋。
她揉着眉心将题纸拍在案上:“老丁,明日去城西监工。”
“小、小姐…”老丁扑通跪地,额头将青砖磕得咚咚响,“老奴定不负所托!”
檐下铜铃忽被春风吹响,惊飞梁间筑巢的燕子。
“小姐,可要再招些外人?”紫莺捧着茶盏轻声问。
沈嘉岁摇头,指甲叩在青玉盏上叮当作响:“外头买的总归隔层肚皮。”
她望着院中散落的算筹,“你且瞧着,不出三日,自有人求着来学本事。”
……
在那些分散的店铺中,每家仅有一名店主和几位帮工,并未专设账房一职。
过去的日子里,由于生意规模不大,账目管理尚属简单,无需特别设立账房。
然而,随着生意的蓬勃发展,账务的复杂度逐渐提升,若不将账房独立出来,恐怕难免会陷入混乱之中。
那么,要从何处觅得一位合适的账房呢?
沈嘉岁正发愁,目光在身旁几位一等丫头身上流转,忽然心中灵光一闪,有了主意。